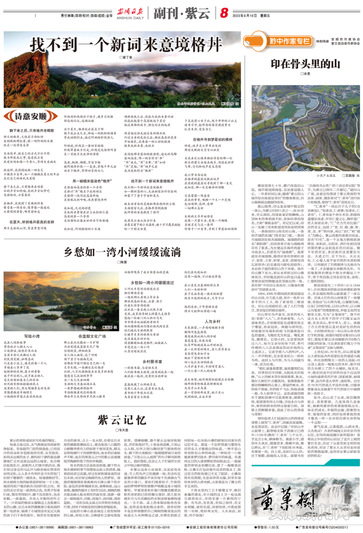
诗意安顺
找不到一个新词来意境格丼
□紫丁香

格凸河妖岩景区-银山风光 □王凯俊 摄
静下来之后,只有格丼在唱歌
烟火的格丼,火烧茄子西红柿
灰刨辣椒烤红薯,蘸一碗阿妈的米酒
就是一道诗意美食
生活简单,按自己的方式不忙不慌
做力所能及之事,想爱就去爱
热爱时间和每一个亲人,等待生老病死
就这样,我悄悄地做一回自己
不傲慢不自卑,如一只猫躺在夏天的午后
忘记自己的姓氏及爱情
静下来之后,只有格丼在唱歌
水的声音如呢喃,花的声音似梦呓
鸟语轻快,云雾柔软
在格丼,我找到了灵魂的伴奏
像青春一样清白,像梦想一般遥远
从黎明到黄昏,唯有静和美
在夏天,听到格丼最真的言辞
那片美丽的山河,常在梦里呼唤
阿妈用针线缝补于绣片,藏岁月荆棘
渺远的记忆,追溯血脉
这个夏天,格丼说出最真言辞
赐予我公主之名,捧起一碗肥肥的酒香
等我回到村庄,接过阿妈的针线活儿
阿妈说,针线是一条回家的路
针线带着故乡行走,针线是忧伤倾听者
是一首被月光洗净的诗歌
高原,枫树,蝴蝶,宇宙万物
被阿妈用针线一一复活,穿越千年之后
端坐于格丼,等待回家的女儿
用一碗糯米饭染色“格丼”
是谁敲响高原的第一个音符
是谁以“丼”赐名于我的村庄
是谁将一段河流高高举起
是谁低沉的呼唤,夜夜萦绕耳畔
我知道,天边的彩霞
是我的亚鲁留在世上永恒的仁慈
高原的第一个音符
是他留给后裔永世的安宁和教诲
我知道,阿妈酿制的小米酒
喝醉夜晚之后,就能与我的亚鲁对话
就能托起整个高原链接于星空
抵达英雄的故乡,讲述村庄的起源
俯身接过祖先递过来的糯米饭
行过古老的礼仪之后,掏出高原的花香
开始染色,我要染一碗七彩饭酿酒
敬奉我的亚鲁,我的王
我唱起那首最初的敬酒歌,遥远的马蹄
敲响高原,唯一的音符为“丼”
“丼”成光,“丼”当舞,“丼”如诗
“丼”是福,“丼”回声之后
成为我的村庄“格丼”
找不到一个新词来意境格丼
找不到一个新词来意境格丼
如一颗坦荡的心,无法融进任何形容词
却装下了整个宇宙和夏天
被生活重伤的灵魂和那些琐碎的尘埃
互相伤害之后,在格丼得到救赎
把所有的妄念执进了暗河
我看见云朵从远古归来
亚鲁王留下的小米酒香,被十万只鹰燕抬起
给一个村庄加冕
于是我将心安于此,做个乖乖的小公主
读书习字,把所有的苍茫藏进骨头
认真生活,宽容自己
在格丼寻到梦最初的模样
昨晚,蛙声是从梦里出发的
那些失眠的文字可以证实
自我决定从格丼掏出诗意的那一刻
村庄的萤火虫越来越多,闯进我的梦
飞舞,它们和蛙声发生恋情
我以梦为马追赶
在格丼的最低处揪出蛙声
在夜晚的最高处寻找到了那一束光
我知道,那一定是格丼的诗眼
它在蓄谋一场盛宴
在我的梦里,唤醒一个又一个灵魂
包括诗神,花神,爱神
一切那么美好
失眠的文字开始诗意
我像一只萤火虫,更像一只蝴蝶
身披月光飞过一条河
停留于一口老井,寻到了梦最初的模样
乡愁如一湾小河缓缓流淌
□陈慧

绿水青山 □张露 摄
写给小湾
我在人间捡故事
有些地方入脑又入心
小道静谧,稻香扑鼻而来
宜居乡村之风拂过人间
村民用笑脸,证明喜欢
行走在小道上,遇见的每一个人
幸福在心里开了花
把飘渺的炊烟,落日的黄昏
说予外出的人,说予故去的人
毫无保留袒露自己的告白
时代的犁铧轻轻翻动泥土
这里的人们,用文明描摹美好生活
用勤劳酿造幸福明天
小城镇的梦想正在悄然绽放
在蓝靛文化广场
群山在此处腾出一片旷野
而后创建成蓝靛文化广场
惊艳的蓝,神秘的蓝
令人陷入幽深,忘了呼吸
俯下身子与植物交谈
仿佛在听落叶倾述自己的一生
文字失聪,一些描述忘记偏旁
此时,人不比植物能生出更多的共情
想想自己流泪的季节
这一生已无法回溯
生活的乏力感汹涌而来
一些梦想被摔得粉碎
手指轻触着风过的路径
那些年久失修的岁月跃入眼帘
旧物件喂养了我日渐苍白的灵魂
乡愁如一湾小河缓缓流过
小河从乡愁馆边缓缓流过
柳杉舞动身姿
一缕炊烟从房顶上窜出来
那些熟悉的犁耙、石磨、筛子
列着队形等待检阅
流水在一条直线上沉默不语
突然,我家拐枣树上掉落几支拐枣
想起一匹破门而入的旧月光
爷爷侍弄他油腻的老烟斗
奶奶借助煤油灯缝补漏风的衣裳
他们彼此不语的默契
打破岁月里的艰难与苦涩
我沿着成长的方向
闭着眼睛细数老物件,细数故人
乡愁是这一湾小河
从身边缓缓流过
乡村图书室
一排排书籍,与爱好无关
人们给书贴上标签,按类别放在一起
被放在一起的,还有村庄的命运
晨露收藏了打碎的月光
没有人来人往,没有车水马龙
看书的少年低头沉思
鸟雀在窗台上假寐
他们在吮吸知识
没有一滴雨,可以淋湿梦想
在以蓝色为基调的村庄里
人们一生的积郁
在于无法参透一滴水的秘密
现实不能到的地方,文字可以
想到这些,少年整顿坐姿
埋头又把命运苦读一遍
人与乡村
天色微蒙,一声鸡鸣唤醒乡村
猴场河氤氲缭绕
匍匐成线吐纳人间冷暖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红马甲给她送来山外的讯息
在一无所有的明天,老人草草老去
未来得及告知子女
她扯下清澈的白布
耐心包扎生活的疼痛
人守护着乡村,乡村哺育着人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在大田堡,她所拥有的稻穗点头哈腰
她所拥有的格桑花娇嫩绽放
无关乎山木鸟兽
在一首诗的命运里,她只关心
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紫云记忆
□韦天罡
紫云的老街道如岁月沧桑的皱纹。
每逢立春过后,天气渐渐显得清新明净起来。华连超市门前的圆盘处,已有绽开的花朵和含苞欲放的花蕾,众芳羞涩,如尚未出阁的女子,婉约而宁静的姿态静静地伫立在这座边远的山城里。东方刚泛起鱼肚白,晨练的人们便开始活动,偶尔穿过身边的马达声与路旁绿化带里的虫鸣交织,让人多少有些怀念当年的东门田坝于堰塘的一湖清水。每逢插秧时节,雨水顺着大地的脉络延伸到每一寸土地,城郊的农户便活跃在田园阡陌之间。雨后的天空尽显一派清纯之色,有燕子衔春归来,梨花带雨初开,脚下浅草萌生,色青如釉,一派蓬勃。在农人辛勤的劳作之下,一片碧绿的秧苗从堰塘边上直抵磨石关的山脚,亘旦水库的灌溉渠日夜流淌的那一泓清泉,装满了小城里没有见过大海的孩子们干净的童年。倘若在有星星和月亮的夜里,点上一支火把,沿着亘旦水库的灌溉渠溯流而上,便会发现八只脚的山螃蟹举着有力的双钳于夜间觅食,肆无忌惮地横行于沟渠野壑间,流水的沿途蛙声不断,处在四围苍山之中的紫云县城便宛若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
有水的地方总是流岚弥漫,脚下的大地在播种的季节里散发出泥土的清香,随着清风穿过岚霭,穿过农家炊烟袅袅的青瓦木房,而后穿过熟睡的农人的梦里。清澈的堰塘倒影着渐渐向五峰山落下的夕阳,金色的余晖铺满水面,垂柳如丝,远山如黛,堰塘的堤岸上有村妇浣衣,娴熟的捣衣姿态映入临水照花的波光里,涟漪一圈又一圈地荡开,回旋,再荡开,再回旋,周而复始。一切在杂乱无章之后井然有序地进行着,时间于顷刻变得沉静而舒缓起来。
远处的五峰山是县城边上造型独特的山脉,形似五指,主峰建有卫星电视发射塔。登峰俯瞰,整个紫云县城尽收眼底,若在秋收时节,十里金风送爽,万里云山入眼,壮怀之情与胸间意气便油然而生,脚下的大地极似一幅缓缓舒展开来的画卷,“万里云山入画图”的句子瞬间跃然纸上。适时登临,总会让人于忙碌的尘世之中得以畅怀襟抱。
在紫云这座小县城里,天还没有亮透,书上的鸟声已经溅落一地,你会听见窸窸窣窣的脚步声来自每个充满烟火气息的小巷口。菜农们挑着担子,竹制的扁担咿呀咿呀的摩擦声唤醒这座小城的黎明。平素里喜欢在巷口摆摊卖酸菜凉粉的老奶奶已经将摊位摆好,那几张充满岁月与生活碾痕的木制桌椅被擦得透亮,一尘不染。桌上的米制凉粉尚有余温,显然是连夜赶做出来的。那些切得不是怎样规整的自己阉制的酸菜发出的味道让人有种暌违之感,仿佛在刹那之间把每一位光临小摊的顾客拉回童年的记忆中去。那是一个怎样贤惠与懂得生活的女人才能做出的味道,一种不是山珍却胜似山珍的味道,一种轻尝一口便能夜夜梦回故乡、梦回童年的味道。有通宵达旦的人揉着稀松的双眼走过,一脸疲惫的神情走到摊位前,要了一碗酸菜凉粉,让摊主打包后便兴高采烈地去了,转过前方的街角便已不见了踪影。小摊虽然有些简陋,生意却异常火爆,时常有身份各异的人群光顾,大家都是为了摊主的手艺来的。
于周末里约三五个略懂文字、略识春趣的朋友,在小城的边上寻一处远离尘嚣的农庄,尽情享受一片难得的宁静。有鸟语,有花香,有知己相伴,有文友相随,谈经论道,诗酒怡情,兴致处悠然一长啸,绝妙两无伦。人生如此、如斯,何不快哉?
印在骨头里的山
□余惠

小湾产业园区 □王凯俊 摄
楼屋重围七十年,棚户改造印山现。城市规划描画卷,宜居建设暖人心。一年多时间以来,随着“紫云印山城市综合体建设项目”的整体推进,印山渐渐露出靓丽的面容。
孤山独秀,印山是县城中独立的一座山,为紫云旧时八景之一,高30余米,峦头圆结,四周悬崖切削嶙峋,山顶林木四季碧绿不枯,形如印章而得名,古称“署临金印”。有记忆以来,印山一直被三角形街道旁的房屋团团围住。一条街因印山得名印山街,一条因古城的东城门得名东门坡,一条因古城墙原址得名城墙路。城墙路的原名“朝阳路”,后因改革开放与海峡两岸有了联系,为方便远在海外的游子寻找亲人,后更名为“城墙路”。我家就住在城墙路,路的对面有供销社房子、雷家、王家、钟家、孟家、原邮电局瓦房宿舍(后交通局与邮电局宿舍)、水站房子遮挡着印山的下半部。虽在印山脚下长大,却从未看到过印山整体面目,平时能见到印山的也只是从周围房屋的隙缝或房顶露出的一角。真有种“不识印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楼房中”的意犹未尽。
1984、1985年期间政府规划建设印山公园,分几批人建,其中一批有10多个四川工人,租了家里的二楼居住。印山公园建好后,成了人们节假日、茶余饭后的娱乐场所。
印山常年鸟声盈耳,居多的有八哥(俗称“八八”),亦有麻雀等。八八通体黑色,矛状额羽延长成簇状耸立于嘴基,形如冠状。两翅与背同色,初级覆羽先端和初级飞羽基部是白色的翅斑,飞翔时尤为明显。嘴乳黄色,脚黄色。记得小时,父亲曾饲养过八八,每当父亲空闲坐下时,乖巧伶俐的八八总是调皮的站在他的头上或肩上。父亲学着八八的叫声,八八一声声附和,总会惹来印山一阵阵鸟鸣。这时人与自然,鸟与人间融为一体,甚为壮观。
“根扎崖逢郁葱葱,暴风骤雨仍从容。四季经历不同难,无限风光在险峰。”山上的树木常年郁郁葱葱,秋天,偶尔几树红叶点缀其间。很难想象在那切削嶙峋的山崖上,翠绿的树木,有的枝干倒悬,有的枝干飞出,特技表演一般,令人惊异不已。这些顽强的树在干涸和贫瘠中压低着树身,顺着风势,根紧紧的伸入石缝,寻找水分与养料,树梢则拼命的伸出接受日照。崖壁上的婀娜多姿,造就了印山的秀丽与苍翠!
曾听起老人们说起印山的西南面崖壁上刻有“仁者寿”,因被房屋遮掩,未见真面目。县志中记载:“在印山半山陡壁上,提督杨天纵于清雍正已酉年(1729年)镌有‘仁者寿’三个大字,字见方2米,柳体楷书。落款小字,惜因年久风化,脱落甚多,模糊不清,难以辨认,在‘仁者寿’下面距地16米处,有摩崖一面。向上看,尤如白云入帘;往下俯瞻,险峻而入目炫。崖壁书有‘兵部尚书云贵广西三省总督记院’等字,为雍正已酉年二月题记。”建印山广场,县委宣传部请了紫云资深的书法家、画家、摄影家对“仁者寿”进行拓片和填墨,使得“仁者寿”重现天日。
“仁者寿”一词出自于孔子的《论语雍也》。“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仁者寿是个养生术语,指那些道德崇高者,怀有仁爱之心,胸怀宽广的人容易长寿。“仁”在古代有比较广泛的含义,包括了“宽、信、敏、惠、智、勇、忠、孝”等内容,而以“亲仁”和“爱人”为核心。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原名“归化”,是一个从鬼方辖地到唐降昆、宋和武、元和宏、清归化到民国时期的紫云县到现在的自治县。数千年的历史,多民族在这里繁衍生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大公无私、仁心爱人是宇宙自然的本质和规律。只有顺应了自然规律与天地合为一体了,才会健康长寿颐养天年。当初杨提督治理这个地方并题这三个字,寄予各民族之间友好往来,亲和、仁爱和团结。
据说清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归化理苗府的张克纶和郗松龄等人,在县城东南的山巅募建了一座石塔。后来人们在印山旁修筑了一座堰塘,营造出“以石塔为笔,以堰塘为砚,以东门田坝为纸,以印山作印,以五峰山为笔架”的理想格局,并取文房四宝镇堂之意,号为“文笔闹堂”。寄予在这方水土养育下的学子们能文运兴盛,步步青云,多中举人、进士。承载了古人的智慧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小时候看到过一本以印山命名的打字机排版、油墨印刷的诗集《印山诗草》,即现在紫云诗词楹联内刊《格凸诗联》的前身,可见老前辈们致力于传承“文笔闹堂”文脉与精神。
上世纪60、70年代,印山曾是紫云人获知县内外重要信息的通道与载体。听比我稍微大一些的人说起:印山顶上栽有一根粗壮的木杆,朝不同的方向绑上了四个大喇叭,每天早、中、晚定时或不定时的向这个边远的小城传递着党的声音、国家政策、新闻广播、县内外重大事件、通知等。出生在70年代的我几乎没有印象,只能靠想象或从反映那个年代的影片中窥探到一些影子。
如今,印山亮了出来,依旧傲然挺立、苍翠葱郁。几度风雨几度春秋,她始终慈祥的看着我呱呱出生、快乐的成长、幸福的出嫁、甜蜜的生育、慢慢的变老,同时也看着我的孩子像我一样一步步经历着生命的每一个过程……
紫气东来,云蒸霞蔚,山清水秀,人杰地灵!古老的城池尘封在岁月的记忆,宏伟的规划翻开新的篇章!苍翠而正年轻的印山印证了这片土地的繁衍生息,印证了从蛮荒到文明的风风雨雨,印证了紫云人从贫穷走向富裕的筚路蓝缕,也将印证紫云崭新美好的明天!
 上一篇:
让食用菌变成农户“致富伞”——记贵州省科技特派员唐金刚
2023-08-18
上一篇:
让食用菌变成农户“致富伞”——记贵州省科技特派员唐金刚
2023-08-18
 下一篇:
“推动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大型蹲点调研采访系列报道”之十一“火红”产...
2023-08-18
下一篇:
“推动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大型蹲点调研采访系列报道”之十一“火红”产...
2023-08-18